李少平 郝伟民
一、黑社会犯罪简述
黑社会为外来语,英语为under-worldsociety,一般直译为“地下社会”、“下流社会”。之所以称之为黑社会是相对阳光政府而言,是指对社会的非法控制,也即是黑社会组织是对社会进行非法控制的组织。黑社会又是指一种具有地缘特点的共同体,是基于地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共同的特殊的犯罪群体'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有组织、秘密地从事走私军火、贩卖毒品、绑架人质、组织卖淫等犯罪活动,聚敛巨额财富,是当今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一种犯罪的最高形态,并且在国际社会,在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机构的官方文件中,均把黑社会犯罪称之为有组织犯罪,联合国大会还将其宣布为“全球性瘟疫”、“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在国际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黑社会犯罪有:意大利的“黑手党”、美国的“14K”、日本的“暴力团”、香港的“三合会”等。在旧中国近代上海的黑社会犯罪达到登峰造极。川尤其是青、洪帮为代表的组织影响最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旨在严厉打击和清除卖淫、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黑社会犯罪在大陆也受到了毁灭性地打击,主要活动范围被迫转移到海外,黑社会在大陆由此也销声灭迹。这对于当时一个刚刚结束战火蹂厢、百废待举、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奇迹。通过黑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化,可以看出黑社会组织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l]犯罪的地域性,也就是黑社会组织均有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势力范围;[2]犯罪的组织性,黑社会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组织纪律、犯罪计划和犯罪目标,黑社会本身就包括了“有组织”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讲,黑社会就是黑社会组织;[3]犯罪的多样性,黑社会犯罪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总是利用各种手段来实现犯罪的目的,因而就决定了其犯罪绝不是单一性的,往往是各种犯罪手段交替或并用;[4]以谋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同时对政治和社会施加影响;[5]对政府官员的依赖性,黑社会在追逐其犯罪的活动中,总是极力以金钱、美色等各种手段拉拢一些政府官员,以利用这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保护自己,从而实现对政府腐蚀和渗透等等。
然而,最近的二十多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的不断繁荣兴旺,与此同时也带了一些消极的因素和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境外黑社会组织对我国的渗透活动也逐渐蔓延,形成了中国“大陆版”黑社会。之所以叫中国“大陆版”的黑社会,是因为他们还处于黑社会的初级阶段,无论是组织形式、经济基础,还是对社会的非法控制上,他们的发展还不够充分,与典型的黑社会还有区别,至少它是不典型、不明显的黑社会组织,但是他们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特点和痕迹。因此,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明确地把这种组织界定为“黑检察实践社会性质组织”。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
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和活动特点,实施的犯罪活动和危害性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其自身的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般应当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组织结构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在组织结构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比较紧密,有一定数量的成员,其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一般都有严格的“帮规”、“家法”等约束组织内部人员的“规矩”,一般也都有较为固定的名称。
[二]经济特征。在经济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大都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聚敛不义之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甚至相当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从小做大、赖以生存的基础。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生存”、要“发展壮大”,必须要有经济基础来支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多为社会无业人员,一般无合法的经济来源,在初始阶段为了扩充自身的实力,总是想方设法聚敛钱财、获取经济利益。有的是靠采取“短、平、快”方式突击暴富;有的是靠暴力垄断市场,以收取“保护费”、“管理费”等为幌子强行索取;有的是靠设立所谓各种名目的公司,强卖强买,“以黑养商”、“以商促黑”等等。他们正是凭借攫取的犯罪收益的支撑,形成犯罪的原动力,才得以实施更大规模、更加肆无忌惮的违法犯罪活动。否则,没有经济条件的支撑,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无法发展和做大的。
[三]寻求“保护伞”特征。在社会背景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经常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向国家机关渗透,收买、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或者直接向国家机关安插成员。这是犯罪集团向黑社会性质演变的重要环节,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其他犯罪的主要特征。从目前查处的案件看,一些犯罪集团或犯罪分子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或者在从小做大的过程中,就逐渐表现出一种对政治的强烈的依附性。一方面,由于这些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积极地实施“银蛋”政策,以贿赂收买、美色拉拢等方式腐蚀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中的意志薄弱者,构筑“关系网”、“保护伞”为其犯罪活动大开“绿灯”,或是为它们的非法目的服务,或者在非法的庇护下,希望能长期地生存和发展而不被揭露,或者在公众面前公开显示其势力;另一方面它们又总是千方百计地渗透到“政界”,为自己捞取各种政治荣誉、寻求各种耀眼的“光环”作为“挡箭牌”,从而以合法的方式掩盖着非法的勾当。
[四]社会危害性特征。在行为方式方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犯罪的地域性。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在一定区域诸如村、乡、镇、县,划定自身的势力范围,进行划片“经营”。二是行业性。在一定行业诸如建筑业、运输业、餐饮娱乐业等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初始阶段,在其行为方式上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它的猖狂和向外的扩张性,积极寻求一种所谓的“秩序”,这就是指的犯罪的地域性和行业性。但是当其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后,初始时所追求的“秩序”逐渐形成,犯罪的表象有所收敛,犯罪向着更为隐蔽的方向发展,其潜在的危害性也更大。
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一般情况下,应具备以上四个特征。四个特征是一个整体。只有同时具备四个特征,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当然,这里就涉及对“一般”的理解。我们认为,这里的“一般”绝不是“降格以求”。即并非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在某些情况,可以缺少其中某一特征而仍然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反,“一般”是指在某种情况下,某一特征可能并不典型,或者可能以其他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如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具备“保护伞”特征的,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四个特征是一个整体,也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依据,只有同时具备四个特征,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犯罪集团区别开来。就“保护伞”特征而言,我们认为,行为人只要有可能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的行为,就可以认定具有该特征,不一定要求有后果的出现。
三、黑杜会性质组织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分[一]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犯罪集团的区别。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与一般犯罪集团,都具有一定的组织性,都是为了实施某种或数种犯罪而建立起来的,都属于有组织犯罪。两者的区别在于:[l]犯罪的组织性程度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具有较大的规模、更高的犯罪效率、较为广泛的影响和反侦查能力的内部支撑体系,控制成员能力较强,有一定的宗旨和目标以及统一的犯罪规划和步骤,犯罪能力也较强;一般犯罪集团在组织性的程度上要低于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都没有一套完整严格的组织纪律,对社会的影响也有限。[2]犯罪的目的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追求对一定的区域或者行业的非法控制包括对经济的控制、对政府的渗透和对社会的控制],以获取非法的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进行多种犯罪活动,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并不单纯是为实施犯罪而存在,其实施犯罪是为了对社会的非法控制,对社会的非法控制又是为了更猖狂地实施犯罪;一般犯罪集团的目的比较明确,目的性强,除追求非法的经济利益外,通过犯罪寻求刺激、满足精神需要,其犯罪的指向具体,如通过故意杀人、盗窃等犯罪行为达到剥夺他人生命、非法占有财物、营利的目的,一般犯罪集团多为单纯地实施某一犯罪。[3]犯罪行为的方式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暴力性特征较为明显,尤其是在实现其对社会的非法控制的过程中,这种暴力性又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一般犯罪集团中除实施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外,并非所有犯罪行为都具有暴力特征,其犯罪行为一般都比较单一。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属于行为犯,只要实施了组织、领导或者参与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构成犯罪,一般犯罪集团犯罪中,有的可能是行为犯,有的可能是危险犯,还有的可能是结果犯。[4]对社会背景的依赖性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背景的依赖性更为强烈,它比一般犯罪集团有更强的构筑''保护伞“、”关系网“的需求,其主要犯罪手段是通过暴力、威胁、物资引诱、金钱收买、美色勾引等渗透到党政部门、公安、司法机关等,寻求政治上的庇护,以达到控制区域实施犯罪的目的。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恶势力的区别。恶势力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它是对社会上一种邪恶势力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概括。这种恶势力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危害社会的稳定。所谓的恶势力,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大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纠合性违法犯罪或组织群体。'3,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相比,具有一些共同点:[l]具有一定形式的组织,有一定数量的成员;[2]具有固定或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3]经常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进行聚众斗殴,寻性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经济秩序等。二者的主要区别:[l]从组织特征看,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骨干成员相对稳定,内部分工也很明确;恶势力的组织结构一般比较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也没有严格的”帮规“、”家法“,纠合性比较强,除组织者外,一般成员不固定,也没有严格的分工。[2]从犯罪的目的和经济实力上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而达到称霸一方,对一定区域的非法控制,因此一般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的支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的目的具有多样性,不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同时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实力作为依托。[3]从社会背景看,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扩充自身的势力范围和经济实力,以达到具有较强的社会对抗性,不断向其他领域进行渗透,有较强的依赖性和”关系网“,一般都有”保护伞“的庇护;恶势力的保护伞和关系网尚未形成,对抗社会的能力不强。[4]从社会危害性看,恶势力一般是以实施危害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为主,影响市场秩序和社会治安,其犯罪的势力范围、地域性危害及后果相对较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明确,要严格把二者区分开来,不能不加研究,不加区别,简单地把恶势力等同或上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随意扩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二者毕竟有着明显差异,根本是在于性质上的区别。只有具各了黑社会性质的基本特征的恶势力,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当然,有些恶势力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可能性极大,甚至可以说恶势力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初始阶段,必须加强打击,防患于未然。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区别。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组织、领导、参与恐怖组织犯罪,都是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根据社会的发展所确定的新的罪名,对遏制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日益猖撅的趋势具有重大意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组织、领导、参与恐怖组织犯罪,在组织形式、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l]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侵害的是特定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危害的是社会的管理秩序,以求达到对特定地区的非法控制;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所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安全,对象是不特定的地区。[2]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的多为经济上的利益和企图对社会的非法控制,而通过这种非法控制以满足其组织内的成员在精神和物质上的需求;组织、领导、参与恐怖组织罪者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制造不安定的因素,企图通过制造各种恐怖事件、恐怖气氛发泄对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3]两者在行为方式和犯罪的手段上也不尽一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多样性,主要通过实施暴力、威胁和腐蚀等手段满足其精神和物质上的需求;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主要是实施杀人、爆炸等非常极端的手段,对社会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对人们在精神上造成一种恐慌,恐怖组织犯罪的破坏性更强、影响力更大,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更大。当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可能演化为恐怖组织犯罪,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有利于控制和防止恐怖组织的出现。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黑社会犯罪的区别。二者的基本共同点都在于均属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并且在犯罪的目的、组织结构、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二者也有区别。其根本区别是程度上的差异。黑社会组织,是一种组织更为严密,犯罪活动更为严密有序,把犯罪作为一种职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组织形式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那样严密,在结构、功能和运转管理等方式上还有差异,黑社会犯罪的特征还不典型、不明显。不典型,即是它还不能向黑社会那样对一个区域形成完整的控制和严格的组织体系;不明显,即是它所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一般较为隐蔽,还不能象国外的黑社会犯罪那样公开化。因此,如果说黑社会组织是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那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则是有组织犯罪的初级形态,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向黑社会犯罪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是黑社会的雏形,己经具有了黑社会犯罪的某些痕迹和性质。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主要还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并非是典型的、完整的黑社会组织。所以,在认定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就不能以黑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与苛求。
四、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其他犯罪的关系。行为人在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时,还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如果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还应当单独定罪并与本罪并罚。这是因为,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往往是与其它犯罪相联系的,它们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联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多与其他犯罪相生相伴。行为人总是千方百计通过某种犯罪行为的实施达到其对社会的非法控制,而非法控制社会又需要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支撑,从而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不断地向社会挑战。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成立,是以该组织中的成员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为支撑,而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又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者为后盾,没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这些犯罪活动就难以成功,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就难以生存下去。黑社会性质组织者与该组织成员所实施的具体犯罪之间是无法割裂的,否则就无法准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本质和危害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把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成员实施的单个犯罪有机地结合起来,客观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内在联系。如行为人在实施了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后,又可能实施指挥贩毒、绑架人质、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显然从行为人行为的个数上分析,应当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对此,我国刑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应当以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贩卖毒品罪、绑架罪、强迫交易罪并罚,凡是参与这些犯罪活动的成员,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适用数罪并罚原则进行处罚。
[二]关于”保护伞“的问题。”保护伞“并非法律上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也是在我国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中所产生的一个”专有“名词。黑恶势力犯罪之所以能够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由小做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犯罪分子与国家公职人员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些犯罪的背后有着一张无形的保护网和一些庇护者。”保护伞“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阻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查处的行为。”包庇“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打击,而通风报信,隐匿、毁灭、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检举揭发,指使他人作伪证,帮助逃匿,或者阻挠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查处等行为。”纵容“一般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负有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
一般来说,负有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几类:一类是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如若这些人员不依法律履行职责,或是滥用职权,拘私舞弊,包庇、阻碍查处黑恶势力犯罪,或是泄露机密,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或是通过枉法追诉、裁判,释放在押人员,拘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方式,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从而达到可能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犯罪的。二类是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履行着政府赋予的各种管理的职责,如工商部门、技术监督部门、税务部门等,如果不依法履行职责,也有可能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三类是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少数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特别是负有领导一个地区查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职责的主管领导,放弃职守,不是积极地组织和领导查禁工作,而是利用职权,或是阻碍查处工作、或是通风报信、或是收受贿赂支持黑恶势力犯罪等等,这些都可以认定为”保护伞“。
[三]关于对犯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处罚的理解。
1.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及其在具体犯罪中的刑事责任间题。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可能不一定直接参加某一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但只要实行犯的犯罪行为是组织、领导者所预谋的,组织、领导者就应当对犯罪组织的成员所实施的他所预谋的全部行为负责。但是,如果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超出了组织者、领导者所预谋的犯罪之外,那么只能由实行犯承担其实施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刑事责任;对于因不了解情况而误人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没有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知情后及时退出该组织的,可以考虑不认定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但是如果参加时虽然不知道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一旦了解真相后仍不退出的,则应当认定构成了该罪。
2.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收益和财产的处置问题。通过各种手段攫取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们正是凭借这些犯罪的收益的支撑,才使其犯罪的规模更大,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大。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同时,根据《解释》第7条的规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从预防犯罪的刑法目的出发,应予以没收和剥夺,斩断支撑犯罪的经济来源,预防和阻止他们再次犯罪。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规定适用财产刑的问题,应当说是一个疏漏。刑法财产刑的运用,一般主要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三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非常明显的聚敛钱财的目的。因此,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处罚,应当增加财产刑的适用。这样有助于有效地打击犯罪,消除其犯罪滋生的条件,从根本上断绝其再生存的基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其他财产型犯罪在获取经济利益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从刑罚的适用上考察,其他财产型犯罪普遍适用了财产刑,如罚金、没收财产等,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财产刑的适用。因此,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聚敛大量财物,在追究犯罪分子的刑罚时,应当同时附加适用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参考文献
[1]参见康树华、魏新文《有组织犯罪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13页。
[2]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474页。
[3]参见张弯《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2001年7月23日《检察日报》第三版。
[4]参见陈兴良主编《刑罚全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238页。
(李少平系四川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北师大刑科院特聘顾问教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郝伟民系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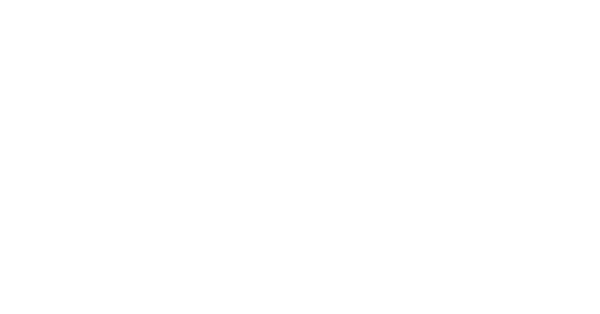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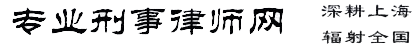
 拨打电话
拨打电话 卢义案例
卢义案例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