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以抢劫罪的构造为出发点
[作者]张梓弦(北京大学法学院)
[来源]《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总第228期)
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已略去原文注释。
摘 要:在界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时,我国既往学说虽能提供一定的解释方向但都存有不可忽视的疑障。较之以人为创设概念的界分模式,从抢劫罪的构造本身出发对其与敲诈勒索罪进行界分才是应循的路径。抢劫罪的内涵并非财产权与人身权的侵犯叠加,而是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创设出了一个与被害人持续对立的冲突状态,进而彻底剥夺了被害人通过利益衡量而回避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处的可能选项,此即彰显了抢劫罪自由侵害犯之构造。基于此,暴力胁迫需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之程度的法理依据实则来源于对“强取”这一概念的解读。在具体判断被害人是否被压制反抗时,可根据被害人自身情状、处于当时环境下的救助可能性及危险圈的脱离等经验素材加以论定。
关键词:暴力胁迫 强取 自由侵犯 对立冲突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是常见多发的财产犯罪,二者手段行为虽若出一辙,但法定刑却云泥之别,因而两罪的界分尤为重要。从近年的趋势来看,两罪界分的探讨虽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实务界及学界始终未能就两罪的界分模式一锤定音。以往,学者们要么采取了拟制要素的方式界分两罪,要么逡巡于两罪具有相似性的构成要件内循规蹈矩。但是,抢劫罪较之其他财产犯法定刑更为严苛之原因却鲜有更深层次的阐明。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相较于以人为创设概念界分两罪的思考模式,从抢劫罪的构造本身出发对其与敲诈勒索罪进行界分才是应循的路径。
一、既有观点的疑惑
(一)当场性说
我国早期观点是基于抢劫罪手段行为及取财行为的“当场性”而提出的界分方向。“当场”的内容涵盖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抢劫罪必须是行为人当着被害人的面发出威胁;而敲诈勒索罪也可以不当面威胁。其二,抢劫罪必须是以当场实现威胁的内容相恐吓;敲诈勒索罪则可以当场实现或日后实现威胁内容相恐吓。其三,抢劫罪必须是当场夺取财物或使被害人交付财物;而敲诈勒索则可以是使被害人当场也可以是日后交付财物。”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抢意见》)第9条规定的“抢劫罪表现为行为人劫取财物一般应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具有‘当场性’”,也从实务的角度肯定了此说的地位。直至今日,这一学说亦不乏支持者。
但是,持此观点的论者既没有指明要求“两个当场”的法理依据;也没有指出什么样的场合才符合“当场”这一基准的内涵。正如学者批判的那样,“‘两个当场’只是形式性的特征,对于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区分,不能根据‘两个当场’,而是应当根据两罪之间的本质界限”;“两个当场”仅仅停留在经验总结和形式归纳的层面上,没有进一步追问和挖掘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法律”。显然,在抢劫罪的条文并没有明文规定手段行为及取财行为的当场性时,此说有过于脱离条文文本之嫌。
实际上,支持此说的论者也并非仅以当场与否来区分两罪,相反,各论者实际上都对“两个当场”施以了若干限制。如有学者指出,抢劫罪需以当场实施暴力相胁迫或其他侵犯人身的方法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或夺走财物为前提,但对于暴力胁迫的程度仍要求“排除被害人反抗”;另有学者指出,“‘两个当场’不是成立抢劫罪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即当场实施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或者准备当场兑现的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性胁迫,并且当场取得财物。”也有部分学者否定了“当场=即刻”的论断,进而主张“被害人身无分文,逼迫被害人到其住宅、办公室等地方取得财物的,也属‘当场’。”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场性说往往与后述暴力胁迫程度说并用,且在暴力胁迫所创设出的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状态持续存在时,亦有肯定“当场性”的余地。
(二)暴力胁迫程度说及竞合说
既然对于“两个当场”的要求不足为凭,那么直接以暴力胁迫程度来界分两罪即成为了另一条路径,此即暴力胁迫程度说。该说的经典表述是,“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必须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的暴力胁迫只要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据此,行为人是否当场实施暴力胁迫或取财并非是界分两罪的标杆之一,“因为即便并非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也完全可能压制对方的反抗,……甲在乙家安放了炸弹,威胁乙三天之内交付100万,否则遥控爆炸的,宜认定抢劫”。
不过,若单纯以暴力胁迫程度的高低来界分两罪,那么上述学说的描述看似是为暴力胁迫的“量”设定了一个“阈值”:仅当处于此“阈值”之上的暴力胁迫程度可该当抢劫罪,而敲诈勒索罪的暴力胁迫程度的量仅能匹配此“阈值”之下的段位。在这个意义上,当暴力胁迫达到阈值的同时,当然也满足了仅要求暴力胁迫程度的量处于下位阈值的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竞合说”便是顺应这一思路的产物。依此立场,“既然以没有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程度的暴力胁迫取得财物的行为能够成立敲诈勒索罪,那么以达到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程度的暴力胁迫取得财物的行为更能成立敲诈勒索罪”。至此,两罪的界分已不再重要,但由于两罪手段行为的程度差异,当暴力胁迫程度不能达到抢劫罪所要求的阈值时,便只能成立敲诈勒索罪。可以说,竞合说的理论价值更多的在于从消极层面筛除不属于抢劫罪的行为类型。因此,竞合说实际上是在暴力胁迫程度说的大方向上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延伸,前者为后者的变体而非彻底独立于后者。
然而,以暴力胁迫为着眼点的分析路径也难免受到批驳。虽说此观点不同于当场性说,其在两罪的构成要件内部找到了一个类同的切入点进行了界分,但正如刑法条文并未规定抢劫罪手段及取财行为的当场性一样,条文也并未对抢劫罪手段行为的程度加以任何细致描述,因而缘何要以暴力胁迫程度的高低作为界分基准同样经不起推敲。批判者指出,“这些以暴力为中心的区分标准本身,既没有实定法上的根据,又不能自我说明其产生的理由,因而尚不能作为成熟的理论标准”。由此观之,暴力胁迫程度说并非不能界分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只是在条文没有为暴力胁迫需达到一定程度提供足够依据时,此说有“人为意定”之嫌。
(三)处分自由说
与上述观点相对,近年来,有论者试图规避单纯聚焦于手段行为的界分标准,进而提出以“被害人处分自由的存否”为核心的区分宗旨。例如,车浩教授认为,“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可被归为两种不同的财产犯罪类型。前者属于压制被害人意愿反抗型,后者属于利用被害人意愿瑕疵型;……体现在对被害人的财产法益支配意愿的影响上面,即究竟是被害人在尚存有处分自由的情况下同意处分财物,还是被害人在完全丧失处分自由的情况下由行为人取得财物;……区分两罪的理论标准,只能是处分自由。”基于此立场,车浩教授进一步明确了作为关键词的处分自由的内涵:“第一层含义是反抗有用,即被害人的妥协和配合是行为人获得财物的必要条件;……第二层含义是应能反抗,即不妥协的代价没有超出被害人应能承受的范围。”
较之于前述观点,车浩教授从体系论层面对两罪加以了解读,相应地也对处分自由的判断标准予以了详述。但是,此说仍未脱离“暴力胁迫程度”的窠臼。且不论在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中拟制一个“处分行为”的前提是否合理,车浩教授将处分自由的内涵解读为“反抗有用”和“应能反抗”,似乎只是用另一套语言逻辑表述了“反抗是否被压制”。从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因果流程来看,两罪的构造在“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被害人财物转移至行为人处”这一层面而言并无表象之差;特别是当两罪都呈现出被害人屈于暴力胁迫而交出财物的情形下,处分自由的存否仅能通过行为人对被害人施以了怎样的暴力胁迫才可推断,因而所谓处分自由的存否无非只是暴力胁迫作用于被害人的程度于规范层面的结果之呈现:即当行为人所实施的暴力胁迫程度彻底倾轧被害人处分自由时成立抢劫,当暴力胁迫程度使得被害人仍残存一定的处分自由时则成立敲诈勒索。若仅以处分自由论及两罪的区分,无疑有从结果推过程之嫌。正如主张敲诈勒索罪不以处分行为为前提的论者所言,“被害人处分只是判断被告人行为之不法内容的辅佐性材料,不能倒过来决定其行为本身的不法性质”。
由此视之,与其说车浩教授的观点与以往的暴力胁迫程度说完全相悖,倒不如说该观点是从另一个视角佐证了暴力胁迫程度说的可行性。依此视角,本文认为,处分自由说与竞合说在方法论层面具有类似性,均是在暴力胁迫程度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变形或延展。
(四)小结
综上所述,既往观点在论及抢劫罪的构造时均离不开“压制反抗”这一关键词。若肯定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须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则相当于承认了这一程度要求本为抢劫罪构成要件内部的制约,而非为了界分抢劫罪与他罪而人为创设出的一个观点。然而,我国抢劫罪构成要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压制反抗”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压制反抗是暴力胁迫程度的彰显抑或处分行为的次位基准同样众说纷纭。在本文看来,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欠缺统一的共识正是源于对抢劫罪构造本身并无更深层次的探究,而抢劫罪的构造则直接关乎其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分标准之设定。
二、问题意识的转向
(一)抢劫罪的构造:财产权与人身权的侵犯叠加?
1.在对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循规求异之前,论者们都未曾真正予以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在诸多财产犯罪中唯独抢劫罪被规定了如此严苛之刑罚?有关此点,传统观点多将其缘由归结为抢劫罪同时侵犯被害人的财产与人身权而一笔带过。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实务界的认可,《两抢意见》第10条规定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便是例证。
不过,除少数观点主张抢劫罪的手段行为须“足以危及被害人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外,传统观点的论者们大多未对暴力胁迫予以绝对的量化描述,而是认为“当场对被害人人身实施并用以排除被害人反抗的,都应属于抢劫罪的暴力行为。”为避免纯粹以“量”论罪的局面,部分学者对前述措辞予以了微调,认为抢劫罪的内涵除侵财之外并不在于对人身权的实际侵犯,而是在于其手段行为具有侵害人身的“高度危险性”。如周光权教授即认为,“(抢劫罪的)行为样态对人身法益具有高度危险性,这是其与其他财产罪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据此,司法解释将行为人造成了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作为抢劫罪既遂的择一标准的合理性有待商榷。此外,车浩教授在阐述抢劫罪的构造时虽未将着眼点置于暴力胁迫概念之上,但对前述观点也未置可否,他认为:“在抢劫罪的场合,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法益支配权的破坏是最严重的,它不仅正面压制被害人对财产法益的支配权,且大多数场合下也对被害人人身形成了威胁甚至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抢劫罪是所有财产犯罪中惩罚最严厉的犯罪的原因。”在此立场下,抢劫罪手段行为的严重性及其时常蕴含的人身危险才是抢劫罪科处如此严苛之刑罚的缘由。
2.诚然,鉴于抢劫罪作为所有财产犯罪中唯一直接规定了“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条款的犯罪,将此加重要件理解为“抢劫罪基本犯所蕴含的人身危险的现实化”似无不妥;特别是抢劫罪中“暴力”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从经验逻辑层面而言也常与人身危险等概念相关联。这也是为什么在犯罪学领域中,抢劫罪被归类为暴力犯罪的直接原因。但是,这样的思考模式所引发的疑惑是,既然人身权是抢劫罪的保护法益,那么是否任何抢劫罪都势必会伴随着人身权被实际侵害的结果?如果将抢劫罪的刑罚高于其他财产犯罪的原因归结于其对于被害人人身所造成的高度危险,那么以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手段压制被害人反抗后的取财是否不符合抢劫罪的构造?显然,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第一,虽然抢劫罪直接规定了“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条款,但由此逆推“抢劫罪的实现必定伴随着人身危险”明显失当。以同样规定了“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条款的强奸罪为例,即便作为结果加重犯的强奸致人死亡可以彰显行为人的手段行为具有对被害人人身造成高度危险的情形,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强奸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必然蕴含对被害人人身的高度危险。换言之,不可能将对被害人人身尚不能造成危险但严重侵害被害人性自决权的情形排除在强奸罪的范畴外。这样的分析结论亦可推及抢劫罪。由此,仅以暴力这一手段行为来看,其所可能造成的侵害人身之危险不过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提炼,而非为抢劫罪手段行为的必然要求。
第二,以胁迫为例,传统观点多认为胁迫意指以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因而胁迫内容本身应彰显“暴力性”。但是,胁迫内容的暴力性和胁迫是否造成了人身侵害或侵害人身的高度危险本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例如,在行为人向被害人展示刀具或枪支以索要钱财等行为中,能够对被害人人身造成实害或危险的并非展示刀具或枪支这一胁迫行为本身,而是被害人拒绝交付财物后行为人进一步的身体举动(用刀刺向被害人或开枪等)。更何况,在行为人只欲以胁迫本身压制被害人反抗而并无将胁迫内容付诸实行的进一步设想时,如何肯定人身权侵害则尤为存疑。如冯玉东抢劫案中,被告人在打工期间得知窦某比较富有,遂携带用鞋盒包装的假定时炸弹敲开窦某家门欲取财。此时,即便被告人展示出了若不交付钱财即引爆炸弹的虚假姿态,但在假炸弹不可能伤及他人的情形下,法院亦无例外地肯定了抢劫罪实行行为之着手。在此思考路径下,诸如以采用药物、酒精等使被害人暂时丧失自由意志的“其他方法”而实施的抢劫,则更加脱离了侵害人身的高度危险之内涵。
第三,如前所述,我国既往观点在界分抢劫与敲诈勒索时虽莫衷一是,但就抢劫罪创设出了“被害人被压制反抗”这一状态而言可谓达成了共识。但显而易见,“压制反抗”也并不必然与人身危险相关联。例如,甲以不可能伤及人身的玩具枪抵住被害人威吓其交出财物,乙以散布被害人裸照相威胁让其交出钱财等事例中,前者因被害人屈于甲的威胁不敢反抗进而交付财物成立抢劫,后者因被害人选择了在财产之上更重视自身名誉的保护而仅成立敲诈勒索。可见,在不存在人身危险的情形下,二者的直观区别在于行为人的手段行为是否使得被害人仍留有一定选择的余地。实务中亦有如下判例为证:被告人毛秀萍和沈云红与被害人赌博时,以被害人“打夹子”为由,打了被害人几个耳光后将桌上的赌资收走,又要求被害人每人赔1万元,并以毛巾抽打等动作和语言施以威吓。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的理由之一是,“抢劫罪中使用的威胁手段,是为了使被害人当场受到精神强制,使其丧失反抗意志,除将财产当场交付外,没有考虑和选择的余地;而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在决定是否交付财物上尚有可考虑和选择的余地。”故此,所谓“压制反抗”并不能直接彰显暴力胁迫的量,而是对于被害人在遭受暴力胁迫时是否还有通过利益衡量而选择“他行为”的可能性之呈现。
(二)自由侵害犯的解读
将目光移至域外,不拘泥于人身危险的理解模式亦能在比较法层面找到相应支撑。
1.德国刑法第249条(抢劫罪)规定:“对他人使用暴力或者对他人身体或生命施以现在的危险之胁迫,以使自己或第三人非法所有为目的而取走他人动产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第253条(敲诈勒索罪)规定:“非法使用暴力或以显著的恶害胁迫他人,强制其实施、容忍或不为一定行为,并因此以使自己或第三人非法获利为目的对被强制者或他人的财产造成损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仅从文本层面而言,德国刑法中的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之程度有所差异,且对于是以何种样态实现了构成要件结果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顺应着这两种界分思路,德国学界也分别展开了两种路径的说理模式。
第一,手段行为的“量化”。一般认为,德国刑法中抢劫罪的规定是由强制罪与盗窃罪结合而成的复行为犯,但较之于强制罪的规定而言,抢劫罪显然是以“加重的强制(qualifi-zierten Nötigung)”作为其手段行为。相比之下,德国刑法中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则与强制罪中的完全相同。基于此差异,部分学者认为,抢劫罪中的暴力概念本身便应被予以更严格地解释为“针对他人身体具有若干严重性的侵害”。这一方面源于抢劫罪较高的法定刑,另一方面也能够使得暴力的程度与胁迫中所要求的“对他人身体或生命施以现在的危险”这一程度相自洽。在此前提下,手段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并非抢劫罪与他罪之界分重点,针对他人人身的侵害的严重程度才是更为合理的界分基准。与此相对,鉴于敲诈勒索罪中对于暴力胁迫的描述与强制罪完全相同,当然也只有不符合抢劫罪中的对人暴力这一手段行为之程度的暴力才可该当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据此,对于他人身体施以绝对的暴力(vis absoluta)进而彻底压制被害人的行为模式自然只能囊括于抢劫罪的范畴之中。
不过,德国理论并没有仅停留在这一步。相反,部分论者虽然得出了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程度要求更高的结论,但该结论背后的深层次思考却不仅仅在于对暴力胁迫予以“量”的层面的描述。如Sander认为,“抢劫罪中对人的暴力应理解为以绝非轻微的暴力对他人所施以的身体强制状态”,但这样的程度要求并不代表行为人所实施的暴力的“量(Ma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相反,“被害人所处的身体强制状态才是问题的核心”。在这样的立场之下,“身体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需要对被害人的生命具有危险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暴力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由行为人所施加的强力必须是抢劫罪中的‘取走’的一个实质构成部分,也就是说,暴力程度必须足够显著,以至于能够压制被害人可能或正在实施的反抗。”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判断抢劫罪手段行为的程度时,并不在于寻得一个确切的“阈值”而将在此“阈值”之上的暴力胁迫后的取财均划归为抢劫,将在此之下的归为敲诈勒索;相反,暴力胁迫所引发的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之状态才是彰显抢劫罪刑罚严苛性的关键点。基于上述理解,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之状态并不直接和人身侵害相关联,抢劫罪中暴力胁迫的施加也不一定彰显了对人身的高度危险。
第二,构成要件结果的“质化”。德国通说认为,就抢劫罪的财产犯属性而言,其与盗窃罪并无二致。因此,抢劫罪构成要件结果与盗窃罪相同,是通过“取走(wegnehmen)”这一行为而得以实现。与此相对,敲诈勒索罪则要求行为人经由手段行为致使被害人的财产损害。因此,仅就形式层面而言,敲诈勒索罪只需存在被害人财产损害这一结果即可,在此之外并不额外需要被害人实施相应的处分行为。部分判例基于此立场,认为两罪之别正是在于各自实现方式之“外观(äußere Erscheinungsbild)”,即检验抢劫罪既遂的标志在于行为人是否“积极取走”被害人财物。如1955年的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等在一家酒馆里遇到了L,在其回家的路上将其拉至无人处并胁迫其交出钱财;L开始时声称自己并无钱财,但屈于行为人对其所施加的胁迫最终交出了自己的钱包,并任由行为人从他的口袋中搜寻出少许钱财。关于此案,联邦法院指出,虽然被告人对L的身体所施加的胁迫行为同时符合抢劫罪及抢劫性敲诈勒索中的手段行为,但“抢劫罪与抢劫性敲诈勒索罪的界分并不在于被害人内在的意思指向,……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是通过行为人取走被害人的财物得以实现,若被害人迫于身体或生命之现实的威胁而自己交出财物的,则成立抢劫性敲诈勒索。”若将这种思路推而广之,敲诈勒索既可表现为行为人取走被害人财物,也可表现为被害人主动处分或交付财物,而抢劫罪构成要件结果之实现仅能通过前者,如此一来抢劫罪则沦为了敲诈勒索罪的特别条款。即当存在行为人取走被害人财物这一外观时,只需考虑抢劫罪的成否便可;仅当诸如“财物的他人性”或“非法所有意思”等抢劫罪特有的构成要件要素无法实现时,才需要额外考虑被害人是否存在处分行为进而是否构成(抢劫性)敲诈勒索。
但显然,这一裁判逻辑并不能够服众,因为这样的界分模式间接导致了抢劫罪存在的意义丧失殆尽。有鉴于此,部分德国学者将争议的核心置于“敲诈勒索罪是否要求被害人实施财产处分行为”这一问题之上。例如,有学者指出,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构造相同,均为“自损型财产犯”,前者是被害人受到暴力胁迫后仍保有些许意思决定自由的空间进而“处分”了财物导致自身财产遭受损失的犯罪(基于瑕疵意思的处分)。但即便从这个视角出发,也并不意味着“处分自由本身”是界分抢劫和敲诈勒索的唯一标准。究其原因在于,从结果的角度而言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自由仍需通过行为人所施加的暴力胁迫对被害人造成了何种程度之影响来加以体现。据此,被害人对于容忍或拒绝行为人所施加的恶害是否还具有“他行为可能性”才是界分抢劫与敲诈勒索的合理方式;敲诈勒索罪中的暴力也不可能是完全剥夺被害人自由的绝对暴力,因为在完全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绝对强制下,被害人不可能保有任何意思决定的自由从而实施法律意义上的“处分行为”。至于被害人的财产转移是以怎样外观得以实现的,则不过只是判断财产处分行为存否的推定证据而已。
与此同时,主张敲诈勒索不应以处分行为为前提的学者也同样意识到了上述问题,进而对抢劫罪本身予以了相应剖释。如Erb基于敲诈勒索不应以财产处分为前提的立场,认为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处于交叉状态,而在这样一种交叉状态中,两者的界分则取决于抢劫罪中“取走”这一概念的解读。详言之,其将抢劫罪中的“取走”解读为“无论财物的占有转移是否介入了被胁迫者的行为抑或无论被胁迫者是否对该财物转移存在一个同意的外观,当被害人横竖都会屈从于无法回避自己的财物被行为人获得的这一结果时,则可以否定存在一个(被害人)同意进而认定取走这一构成要件要素的成立。”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处分行为不过是抢劫罪中取走行为的“镜像反射(Reflex)”,肯定处分行为的存在实际上只起到了从反面否定抢劫罪中的“取走”的作用。持类似观点的Küper指出,抢劫与敲诈勒索的界分并不在于承认敲诈勒索必须以财产处分为前提,而是在于抢劫罪构成要件的重构:“抢劫罪是通过暴力胁迫而实现的空间与人物关系层面的直接对峙,被害人直接屈从于心理或生理层面的强力,从而致使行为人获取财物的外形在这样一种对人的暴力状态下已无关紧要;即在这样一种强占侵袭的状态下,财物是被交付抑或取走,被害人是完全介入了财物转移的过程抑或不可避地介入了其中,或财物转移是被直接引起抑或间接地被变为可能,都已不再重要。”总之,当行为人所实施的暴力胁迫能够达到完全排除被害人回避占有转移的可能性之时,无论最后财产是以怎样的外观得以转移,都可以肯定抢劫罪中“取走”这一构成要件要素的成立。
通过分析可见,无论敲诈勒索是否应以存在一个财产处分行为为前提,被害人处分自由的有无只不过是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最终结果,这一最终结果可以借助但并不必然以财产转移的外观来加以判断。相反,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创设出的被害人对于财物的占有转移不具有回避可能性之状态才是区别两罪的核心。可以说,抢劫罪的实现便是通过行为人的暴力胁迫这一手段行为,经由其所激发的被害人对财产转移不具回避可能性的状态这一中间结果,进而使得行为人可利用被害人的前述状态并通过任意的行为样态致使财产发生最终转移。与单纯人为地创设出一个界分抢劫与敲诈勒索的基准不同,这样的思考模式决定了如何解读抢劫罪中的“取走”才是解释论的关键。故此,抢劫和敲诈勒索的界分便由两罪于构成要件层面的差异之问题转向了抢劫罪内部的问题。
2.日本刑法第236条规定:“使用暴力或胁迫强取他人财物者,以抢劫论,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第249条规定:“敲诈勒索他人而使其交付财物者,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与我国相同的是,日本刑法在抢劫罪中明确规定了手段行为的样态,而在敲诈勒索罪中仅使用了简单罪状的描述方式。正因此形式层面的类似性,使得我国和日本在两罪界分的问题上也呈现出了类似的理论分歧和构成。例如,部分学者同样认为抢劫罪具有财产犯和人身犯两个侧面,进而认为抢劫罪在财产犯属性外同样具有“侵害人格法益之罪”的特质。至于界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具体路径,日本学者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一例外地将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与否作为了绝对的标尺。
但在通说的浸染下,日本学界仍存在不以压制反抗与否为着眼点的见解。例如,嶋矢貴之通过分析日本逾百年的司法判例,对不同阶段的实务界动向进行归纳后,将抢劫罪的刑罚较之于其他财产犯罪更为严苛的原因归结于“抢劫罪中对于被害人人身保护之要求更高”。基于此,嶋矢教授认为,抢劫罪中的暴力应限定为针对人身具有高度危险之暴力,而抢劫罪中的胁迫内容也相应地应限定为重大恶害之告知,在此之上还应考虑胁迫者的真意及胁迫内容的实现可能性。即只有客观实现可能的、具有现实迫切性的重大恶害才可该当胁迫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与此同时,暴力胁迫所诱发的被害人抵抗行为同样蕴含着伤亡之危险,在这一状态下,抢劫行为所引发的是一个行为人与被害人持续对立的冲突状态,且这一冲突状态也伴随着随时扩大规模之风险。若能肯定前述要素,方可认定抢劫罪而非敲诈勒索罪的成立。此时,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与否已不再是抢劫罪的必要要件。这一观点作为对日本自旧刑法以来实务动向的全方位归纳自有其理,特别是嶋矢教授将抢劫罪的构造描述为“行为人与被害人持续对立的冲突状态”这一点来看,既能含摄一般人对于抢劫罪构造之设想,也可与事后抢劫罪中强调“盗窃机会的持续性”达成自洽。
不过,对抢劫罪中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对立冲突状态这一描述虽然精准,但若对抢劫罪手段行为施以如此严苛的解释,则有着过度限定之虞。在嶋矢教授的观点下,诸如以精巧的玩具枪佯装真枪胁迫他人交出钱财、或通过轻微暴力制服醉酒之人后取财等完全可以压制对方反抗的行为都不可能成立抢劫罪。应该说,所谓的针对人身之高度危险,只不过是以抽象危险之形态消融在了“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暴力胁迫”这一要件的理解中,其不过是被害人被压制反抗的“通常附随效果”。
基于上述逻辑,日本学界此后的争议点仍回归至了“被害人被压制反抗”这一轴线,只不过,单纯论及暴力胁迫程度的观点已式微。如芥川正洋认为,抢劫罪的构造并不在于侵害人身权的高度危险,而是在于“自由之侵犯”。此时,自由的内涵并不在于被害人可为其所欲,而是在其直面暴力胁迫时可否保有“选择”:“所谓抢劫,是通过暴力胁迫剥夺了对方的行动选项,而使其陷入除忍受财物的占有转移外再无别的行动选项的状况之中,……此即为抢劫罪作为自由侵害犯的不法内容。”与此类似,桥爪隆指出,抢劫罪中所谓的“被害人被压制反抗”实际上是对“财物、利益的转移是否具有回避可能性”的判断,因此,被害人被压制反抗这一事实与敲诈勒索罪中行为人不存在一个交付行为实为同义反复;基于此,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被剥夺时,违反被害人意思取得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才是抢劫罪“固有的法益侵害性”。
同时,实务中以“被害人是否具有其他的行动选项”为据的判例早已有之。如1963年的一起判例:被告人等将一名女性围住,并要求她交出钱财,与此同时将该女性手腕握住,并用白杨木将其顶住,随后取走了内有5000日元的被害人的钱包。本案法官认为,“该女子从现场逃走,或者向他人求救是极其容易的,即便考虑到该女子精神和肉体层面的苦痛,若认为本件判例中的暴力的程度符合抢劫罪的暴力胁迫也是不当的。”再如1969年的一起判例:两名被告人欲强奸被害人而对其施以了暴力,被害人因感到了危机而逃脱的同时,被告人等在其身后紧追不舍,此时被害人表示“我有钱给你,你放我走吧”,被告人等随即取走了钱财。法官最终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仅构成敲诈勒索,其理由在于“交付钱财时被害人仍然有着持续抵抗的余力,且处于一个可以获得救助的状况,只是其没有选择救助而是选择了遵从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其仍然可以选择单独逃跑”。
由上可知,实务界的立场与学者们所描述的“行动选项的残存”这一视角近似。循此思路,即便行为人使用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等看似能够危及被害人人身的手段但并没有完全剥夺行为人的他行为可能性时,也不代表就可直接肯定抢劫罪的成立。实务中亦有例证如下:两名被告人用折叠刀于室外胁迫一对情侣,要求其交出钱财。本案法官指出,“被告人展示了10厘米长的折叠刀,以此触碰男方被害人的膝盖或将其在被害人眼前摇晃,进而要求被害人交出钱财,能够认为被害人无法判断若不按照要求交出钱财会遭受怎样的危害,因而基于恐惧而如前所述交付了钱财;但前述被告人的胁迫行为就压制被害人的自由意志及压制其抵抗这一层面而言是证据是完全不充分的。”
3.综上可知,德日学界对抢劫罪保护法益的探讨由人身权向意志自由的转向,标志着本罪的实质在于“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创设出了被害人反抗压制之状态,进而对被害人能否通过利益衡量选择除财产转移外的其他选项这一层面的自由予以了剥夺”。只不过,作为被害人自由被侵害之表现的“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之状态”是应理解为暴力胁迫的程度描述还是抢劫罪中强取行为的实质基准或仁智互见。但无论作何解,在扬弃了抢劫罪除财产权外还保护人身权这一并不恰当的描述后,即便认可压制反抗应是暴力胁迫的程度描述,其也不过是对强取行为予以实质解读后的折射结论:亦即,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程度之所以需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是因为只有在被害人基于利益衡量的选择自由被剥夺状态下的任意形式之财产转移才可符合抢劫罪中强取这一构成要件要素。据此,上述比较法的引介也旨在表明,正因抢劫罪在侵犯财产的同时彻底剥夺了被害人对于自身财产应处于何种状态的意思决定及就财产转移与否进行利益衡量的自由,才有了较之其他财产犯而言更高的可罚性基础。
不过,此处所谓“自由”并非是在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中拟造一个“财产处分”的概念进而以处分自由去界分两罪,而应将“自由”理解为抢劫罪构成要件内部的制约。换言之,即便不认为敲诈勒索应以“财产处分”为要件,抢劫罪仍应按照前述观念加以理解,这也是基于抢劫罪的构造本身而塑造的“应然结果”。此时,抢劫罪所保护的“自由”的内涵即可理解为“除将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外的其他选择可能性”。
三、“暴力胁迫”与“强取”概念的形塑
(一)“强取”与“窃取”
如上所述,日本刑法明确规定抢劫罪目的行为为“强取”他人财物。我国刑法第263条所称“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看似没有“强取”二字,但对其中的“抢劫”唯有做“强取”之解才可达成文理层面的自洽。原因在于,若认为“抢劫”二字同时蕴含了手段与目的行为之描述,则在第263条的文本中无额外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之必要。正因如此,我国学者多将抢劫罪目的行为定义为“强取”或“强行劫取”公私财物。
就抢劫罪的目的行为而言,我国刑法并未采用和盗窃罪相同的描述,因而在解释本罪目的行为时,不一定需要将其与“窃取”等同视之。不过,我国学者多立足于抢劫罪的财产犯属性与盗窃罪并无本质差异这一立场,而对强取与窃取均采取了“行为人违反被害人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这一抽象化的定义。以体系论的角度视之,这一定义或毋庸置疑,但其仅体现了抢劫与盗窃在“被害人意志违反”这一层级的共通性,而忽略了两罪在实行行为样态上可能存在的差异。就窃取概念而言,学界一般对其具体的方法和样态没有过多限制,除类似于“乘机拿走他人银行卡到银行取款”等通过积极的手段取走被害人财物之典型设例外,“以欺骗手段造成占有者对财物支配力松弛,违反其意思取走财物”,“行为人伪装成顾客到商店试穿高档西服,然后逃走的”,皆可构成盗窃罪。从中亦可知,学界对于窃取难以提炼出完美且具体的定义,因而多以列举的方式阐述这一行为样态的多元化。不过,从各种措辞中可洞察的一点是,即便窃取所表现出的外观各异,但其当然不可能通过被害人主动将财物交付至行为人而完成;从这个角度而言,虽难以通过正面列举的方式穷尽窃取的定义,但完全可以在反证的视角下得出“被害人主动交付财物”这一举措不可能符合窃取的语义逻辑及规范内涵的结论。
循此反证思路,当被害人将财物主动交付至行为人时,可能构成的财产犯仅为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及抢劫罪。在前二者中,被害人是在具有瑕疵意思或他行为可能性的情形下实施了主动交付,该交付行为也可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处分行为,但抢劫罪中的交付则是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不具有自由意思的情形下的被迫交付,具有交付的外观但不能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处分行为。基于这一分析可得出的结论是,抢劫罪并非是人身与财产法益之侵害的单纯叠加,亦非暴力胁迫与盗窃罪的粗略拼凑。抢劫罪中的“强取”这一实行行为的射程实际上要广于盗窃罪中的“窃取”,前者不仅包含了与窃取类似的由行为人主动实施的打破被害人对自身财物的“封锁支配”的积极行为,还包含了以暴力胁迫等方式使被害人陷入被压制反抗之状态后主动解除或放弃对于财物的封锁支配而迫使财物转至“开放状态”的情形。相反,盗窃罪中的窃取则仅能够通过行为人积极地侵入被害人的财产领域内得以实现。
(二)“外观”与“实质”
如此理解抢劫罪中的“强取”,自然决定了“强取”是以怎样的外观得以呈现便无足轻重,其也无法单独彰显抢劫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的特征。此时,因行为人的暴力胁迫而驱使被害人将原本对自身财产的封锁支配转至的开放状态,决定了财产转移不再需要行为人积极的能量投入便可完成,消极收受开放状态下的被害财产任意形式的流入亦为可能。因此,除与盗窃罪中窃取行为近似的“直接夺走被害人占有的财物”之情形外,诸如“被害人主动交付财物”“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行为,乘被害人没有注意财物时取走其财物”“在使用暴力胁迫行为之际,被害人由于害怕而逃走,将身边财物留在现场,行为人取走该财物”“行为人在未支付价款前打晕出租车司机以逃跑”等,均可成为抢劫罪的目的行为(即强取)。
有关于此,学界多认为此问题涉及抢劫罪中暴力胁迫与取财之间必然存在的因果关系。但实际上,此问题亦关乎抢劫罪的构造本身。如前所述,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都可呈现出“被害人主动将财物交付于行为人”的外观,因而界分二者的关键不在于交付这一“点性状态”,而是在于行为人何以使得被害人交付财物这一“线性过程”。依本文观点,抢劫罪中行为人所创设出的与被害人持续对立的冲突状态可描述为,被害人在直面行为人所施加的暴力胁迫时,通过利益衡量而回避自己的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处的选择可能性已皆无,因而在丧失自由的情形下不可避免地放弃了对自己财产的封锁支配。在这样一种被害人对于财产转移方式以及转移与否完全不具有任何自由意志的情形下,就可将抢劫罪中的行为人视为“利用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之状态”进而获取财物的间接正犯。特别是在抢劫罪的最终环节表现出与敲诈勒索相同的“由被害人主动交付财物”时,抢劫罪的构造决定了其区别于敲诈勒索罪的标志即在于“行为人剥夺了被害人对于财产转移的回避可能性及除财产转移外的他行为可能性”,这一分析结果也与前述自由侵害犯的解释方向相符。
据此,在我国抢劫罪条文未对暴力胁迫的程度有所着墨时,要求其程度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法理依据实则来源于对于抢劫罪中“强取”的解读。即在判断抢劫罪成否时,不能将暴力胁迫和强取行为割裂开作为两个不同的层面加以判断,而应将后者规范化地解释为“在被害人对自己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处不具有回避可能性之状态下的任意形式的占有、支配转移”。从此角度而言,压制反抗当然不是抢劫罪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而应作为抢劫罪实行行为的“强取”要件的实质基准;正因被害人处于前述状态下,才决定了行为人可通过“强取”的手段完成抢劫罪既遂的一环。相比之下,敲诈勒索罪中的暴力胁迫应被表述为,“在被害人对于自身财产之支配保有他行为可能性的情形下,影响了被害人实施有利于自身财产的维持或增加之利益衡量选择”,因而此时被害人所实施的财物交付或默许行为人拿走财物等行为当然不可能被评价为“强取”,被害人是否产生真实的“恐惧心理”业已非决定性要素。而除被害人自由的侵蚀程度尚未达到前述状态的情形外,若行为人本没有通过暴力胁迫创设出任何与被害人的持续对立冲突,而只是通过主动打破被害人对于财产的封锁支配获取了财物,那么则相应成立盗窃或抢夺。
四、自由侵害的推定素材
承接上述结论,余下的问题应是,当以怎样的次位基准去判断抢劫罪中的“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之状态。显然,在判断被害人反抗是否被压制时不能仅凭行为人或被害人的单方供述加以定夺,往往还需借助“外部的客观情状去认定甚至推定难以直接证明的构成要件要素”。因此,对推定抢劫罪被害人是否被压制反抗的可能的客观情状进行筛选之过程不可或缺。
(一)被害人视角下的财产占有、支配丧失回避可能性
在判断被害人是否被压制反抗时,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以“谁”的视角为基准进行判断。学界对此存在着主、客观说之争。前者主张以被害人对于暴力胁迫的感观为基准判断反抗被压制与否,后者则基于理性一般人的视角。
例如,持客观说的周光权教授认为,“行为人客观上没有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即使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特殊情况熟知且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但由于暴力、胁迫程度较轻,欠缺抢劫手段的定型性,不存在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实际上,这样的论断往往并非指向的是在判断抢劫罪实行行为时将被害人的特殊情况等作为判断基底的思考路径,而是在指向行为人仅实施了在一般人看来完全不能压制他人反抗的轻微暴力胁迫时仍该当抢劫罪的看似违和的结论。若顺应客观说的思路,任何为压制懦弱者所实施的轻微暴力胁迫都会因为欠缺“定型性”而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因而这类人实则被排除在了抢劫罪的保护范围之外。除却胆小懦弱者,诸如行为人意欲抢劫已醉酒但尚能活动之人而使用了轻微暴力既将其制服后的取财亦不成立抢劫罪。显然,这类观点仍未摆脱掉认为抢劫行为本身就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这一传统观念的桎梏,从而不当地缩小了抢劫罪的处罚范围。
又如,车浩教授并未拘泥于采取统一的客观说或主观说来解决所有涉及两罪区分的问题,而是以行为人是否取得财物为准区分了两套不同的判断模式:在行为人尚未从被害人处获得财物时,因未出现财物实际转移的结果导致区分两罪只能回溯暴力胁迫之程度,此时应以理性一般人的标准来判断暴力胁迫是否达到排除处分自由的程度;而在行为人获得财物时,就可根据被害人实际感受来判断处分自由的存否。这样一种二分法在车浩教授注重被害人处分自由的语境下全然自恰,即当不存在一个处分的外观时,判断基点只能回归暴力胁迫本身;而当存在一个处分的外观时,相应的该处分一定是由特定被害人而实施的处分,自然也应根据特定被害人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决断。但问题在于,处分自由与暴力胁迫程度及其判断方式的关系并非由前者的存否而推断出后者,而是理应由后者的程度及后者是否导致了被害人被压制反抗的状态进而推断出前者;以处分自由为核心将暴力胁迫划分为二元的判断模式有从结果推过程之嫌,此点已于前文指明。此外,就行为人施以暴力胁迫却没能取财予以判断时,车浩教授特别指出,“既没有给无所畏惧的勇敢者什么特权,也不会特别地去保护那些在相对无害的压力面前,仍然以不理智的愚蠢方式随意屈从的人。”然而,被暴力胁迫压制反抗的被害人并非都可用“在相对无害的压力面前仍以不理智的愚蠢方式随意屈从的人”这一描述来一笔带过,相反,完全可能存在理智沉稳但因年龄或自身能力而导致不得不屈从于轻微暴力之人,为何将这类人也排除在抢劫罪的保护范畴之外仍有待商榷。
实际上,客观说论者的立论核心并非在于排除对怯懦者的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持客观说的学者在坚持理性一般人的基准上仍对这一判断予以了具体化,即“暴力胁迫的样态、手段、时间、场所、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人数、年龄、性别”等因素同样在考虑范畴内;真正支持客观说论者的问题意识在于,暴力胁迫本为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于这一要素的判断自然应以客观的基准为尺度。但如前所述,所谓“被害人被压制反抗”这一状态本不是暴力胁迫的“程度标尺”,而是实为抢劫罪中“强取”这一要件的实质基准。顺应此思路,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应是基于“和行为人处于对立冲突状态的被害人可否通过利益衡量对自己的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处尚存选择可能性”的判断,而非“暴力胁迫程度高低”的判断,这也是本文观点区别于传统客观说的关键。因此,以被害人为视角的考量并非会瓦解暴力胁迫作为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存在,相反,这一思考路径恰彰显了只有在与行为人对立冲突状态中的特定被害人被压制的状态下,抢劫罪中“强取”才可能实现的分析范式。这与在讨论因果关系时,将被害人的特殊要素也包摄于实行行为的危险判断中加以考量的路径趋同。相应地,当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特殊性格、体质及能力等并不明知时,则欠缺一个抢劫罪的故意。
例如,A蹲点发现B经营的一家商铺每日傍晚都会交由B十岁的儿子C来看守,因而找准时机趁只有C一人时对其施以极轻微的暴力并强令其交出当天的营业额,而C则因自己和A的力量悬殊不敢反抗被迫交出了财物。此时,即可肯定A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再如,甲因手头缺钱而产生了勒索路人的想法,逢乙路过时,甲对其怒目圆瞪并说道“给点钱花花”;乙因年幼时目睹黑社会上门索债未果将其父殴打致死的场面进而诱发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他人索要钱财极度惧怕,于是在高度精神压迫下将身上全部钱财交予甲;此时,甲虽然看似实施了一个压制反抗的胁迫行为,但由于甲对于乙的特殊体质并不知晓,因而不具有抢劫罪的故意,仅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即可。综合前述设例,在实务中,或许不宜将行为人是否使用能够致死伤的工具等对人身造成高度危险之表象作为抢劫罪成立与否的推定基准的观点弃若敝屣,但这并不代表前者和后者可互为推导。正确的分析路径是:当行为人使用足以致人死伤的强度暴力时往往可推定抢劫罪的成立,但当因被害人性格、能力等特殊情状例外地导致了该暴力没能压制其反抗时,方可否定抢劫罪既遂;若行为人仅对被害人施加了欠缺危险性之暴力胁迫时往往也可推定行为人并未实施一个抢劫行为,仅当被害人性格、能力等特殊情状而例外地导致了其被压制反抗后且行为人对此明知时,方可评价为抢劫罪的实行行为。至此,单纯对暴力胁迫予以量的层面的描述已不再是抢劫罪成立与否的积极要素及实践要领。
(二)救助可能性的存否与危险圈的脱离
随之而生的问题是,当被害人自身不具有对于财产占有、支配丧失的回避可能性之时,是否毫无否定抢劫罪成立的余地?本文认为并非如此。正如前述客观说的论者所言,客观的判断理应具体化为“时间、场所、被害人年龄、性别”等具体的次位因素。其中,被害人年龄、性别等直接关乎被害人自身在对立冲突状态下的他行为可能性之定夺,而时空场所等则塑造了该被害人所直面的“具体的、个别化的处境”。依本文观点,当容忍财物转移至行为人处并非被害人的唯一选择,与此同时,其能通过他人的救助脱离与行为人的对立冲突状态的危险圈从而回避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处则是判断抢劫罪成否的另一个经验素材。有如下判例为证:
被告人蒋金秋将被害人等挟持,以被害人欠赌债为由,让其按事先拟好的内容写下一张借款人民币8万元的借据,并扣下其轿车作抵押,要其两天内还清欠款才将车归还;当日,被告人蒋秋金安排被告人傅金生等人在客房看住被害人后便自行离开。被害人乘傅金生等人熟睡之机,逃出该客房并报警。虽本案的被告人实施了监禁、胁迫等行为,但法官认定被告人不成立抢劫罪而成立敲诈勒索的理由在于,“从本案看,地点发生在宾馆,被害人在被告人等人开房时完全可以报警,……完全可以利用当时的环境采取求救、报警等方式进行抗拒”。
同时,实务中也存在着既已脱离对立冲突状态这一危险圈的被害人仍交付财物的情形。例如,被告人何木生因女友被父介绍嫁往广东,遂起向女友之父要钱之心,与何元达、何东仁一起到其女友之父兰桂荣家。兰不在家,何木生对其妻子和女儿拍了照。在返回的路上,何木生将兰桂荣拦下,要兰赔偿其4000元,并对兰拍照。兰拒绝赔偿后,何良清踢了兰一脚。兰桂荣见状就说:“有什么事到家里去好好说。”到兰桂荣家后,兰说没有钱。何木生说:“不拿钱我不怕,照了你们的相,会有人来杀你们。”接着,何良清又拿出菜刀,让兰把手指剁下来,兰桂荣即到外面向他人借了2000元交给何木生。本案一审法院认定,“被害人被迫独自外出借钱给被告人,此时被害人完全脱离了被告人等的控制,本可以向有关部门保安,但在又怕日后遭到被告人等的报复的情况下向他人借齐2000元钱给被告人,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这一段描述则完全符合前文所主张的,被害人脱离与行为人的持续对立冲突状态这一危险圈后,是否可以通过利益衡量而做出回避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出的其他选择的判断模式。
相反,当行为人不给予被害人通过利益衡量而选择财产转移与否的余地时,即便时空要素持续延长,也不妨碍抢劫罪的成立。如行为人打电话告知被害人两天之内筹齐50万元,并安排了若干狙击手轮番监视被害人的住宅,一旦发现被害人报警、逃跑或未筹集钱款则立刻扣动扳机,被害人只得通过网络转账交付了钱款。在这一案例中,行为人虽留给了被害人相应的时间和空间,但这一时空要素于被害人而言是无益的,因为无论其在这样一种时空制约内作何反应,都会因保全性命而屈从于狙击枪内的子弹。此时,诸如被害人可以利用摩斯密码、通过光线反射发出求救信号等情形也绝非毫无可能。但是,这一环节的判断还应是特定被害人处于特定时空下的真实感观之判断,而非任由第三人处于无知之幕后的居高临下的评判。因而,在机敏勇武者看来可伺机寻求外界救助的情形,不一定能够匹配具体案件中的特定被害人。
综上所述,救助可能性及危险圈的脱离可以作为“被害人是否对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处是否还具有选择可能性”的推定素材之一,只不过,实务可以借助但不必然依存于上述判断模式。亦即,上述判断模式不过是他行为可能性的“实践体现”,最终着眼点仍需追本溯源,回归至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与否这一抢劫罪中间结果的实质化构思。
五、余论及展望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分问题,说到底是在考验解释者对两罪构造有着怎样的深度解读。本文采用以抢劫罪构造为出发点的方法论路径,正是深知为不同罪名划清场域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各罪的边界予以探求。此外,一个更为长远的意义在于,依既往界分两罪的观点而塑造的抢劫罪形象均仅能用以描述刑法第263条,而却无法对刑法第269条事后抢劫罪予以形塑。如着眼于暴力胁迫程度的论者会对事后抢劫中的暴力胁迫同样提出“压制反抗”的要求,但在被害人对自己的财物予以追击时却不存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反抗行为;至于处分自由的剥夺等,则在行为人已取得被害人财物后也不具有了任何可用以塑造事后抢劫罪的理论价值。但是,本文观点却可在此之上另辟蹊径。
现有文献中,“实践中多发”“对人身法益的侵害与抢劫罪类似”等是论者们为拟制事后抢劫所赋予的惯常理由,但这些理由要么不能框定事后抢劫罪的边界,要么落入了前文所批判的以人身侵害论处抢劫罪实质的穴隙。晚近有论证指出,事后抢劫的性质在于行为人获得财物后以暴力胁迫阻碍被害人行使返还请求权。这一说理模式或能契合前行为既遂的场合,但我国的事后抢劫显然还囊括了前行为未遂而为抗拒抓捕施以暴力胁迫的情形,若想要对此二者加以统一说明则无法仅从阻碍返还请求权的角度切入。如何求得统一的说理模式?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此时仍需立足于被害人视角加以论定。
以被害人的角度视之,无论行为人是否取财既遂,事后抢劫无疑仅在被害人自身或与其立足于同一救助阵营的第三人(如警察或目击证人)对行为人实施基于紧急权的追击行为时得以生成。因此,此时的暴力胁迫便不再牵涉反抗或处分等关键词,而是直接指向“被害人选择行使紧急权或是否继续行使紧急权”之自由的制约。同时,诸如前行为为夜间入户盗窃等场合,行为人是否物色到了财物于被害人而言或不可即刻探知,乃至被害人察觉有人侵入时便可直接上前追击。在此情况下,处于被害阵营者对行为人的追击权并不会因不知晓前行为既遂与否而萎缩。据此,事后抢劫的不法内涵则在于,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对于被害人等选择是否或怎样实施基于紧急权的追击可能性、或在行使紧急权过程中对被害人等是否继续行使该权利的选择可能性予以了剥夺。基于此自由侵害犯的构造,此时的暴力胁迫同样无需达到对人身造成实害抑或高度危险的程度,而是在于对被害人行使紧急权的自由的遏抑;诸如行为人在逃跑时施以单纯防御性的追击排除行为等(如挣脱),则因该类行为并非指向“被害人意志或行为选择”之制约而并不具有自由侵害之特质。这也从实质层面诠释了《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所称,“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不以抢劫罪论处的法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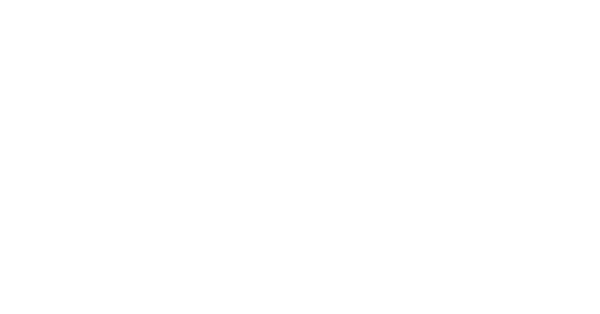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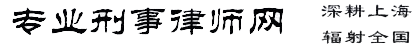
 拨打电话
拨打电话 卢义案例
卢义案例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